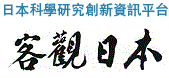這一年是中國留學生最難的一年。
隨著全球疫情的大放大,國際航班及入境管控發生變化。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留學生如何抉擇:是回國好還是不回國好?成為關注的焦點。隨著疫情的發展,中國國内出於對境外疫情「倒灌」的警惕,對於留學生是否應該回國充滿爭議。此前,媒體上更是爆出留學生回國一票難求,有留學歐洲的小留學生甚至十幾萬人民幣一張機票包機回國,讓人唏噓不已。
那麼,這其中日本留學的情況如何呢?
相較於歐美諸國,日本地緣優勢,為中國留學生抉擇提供了便利。「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中國武漢疫情發生之初,中日兩國共同抗「疫」,讓兩國間感情升溫;加之日本人的自律……這些都讓中國家長感到安心。從這點上看,留日學子是幸運的。
疫情下,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主要有三類:第一類學生早在疫情之初便利用春假回到國内;第二類則是選擇呆在日本;第三類是處於等候簽證中的「準留學生」,即4月生。根據目前疫情的發展,多數大學選擇延期到4月末或5月黃金週後開學。
儘管如此,疫情帶來的諸多不確定性,仍讓中國留學生不同程度地感到焦慮:日本國内的感染人數每日還在不斷增長,如何有效地保護好自己?4月入學何時能夠拿到簽證?什麼時候能去日本上學……帶著這些問題,近日我採訪了留日神經科醫學專家,中國心理衛生協會所屬内觀學組常委委員夏寒松先生,請他從專業角度,並結合自身經歷,為中國留學生抗「疫」支招。夏醫生擁有10年日本留學和工作經歷。武漢疫情發生後,他曾多次「臨危受命」負責接回滯留在海外的湖北武漢籍旅客。
武漢疫情放大後前後三次「護航」
認清「新冠」,合理應對
作為一名專業醫生,夏寒松認為留學生首先是要認清「新冠」,如此才能合理應對。武漢疫情放大後,夏寒松總共二次隨專機「出征」,將滯留在新加披和日本的武漢籍旅客接回中國,並船團護航回武漢。除此之外,還有一次是將滯留在武漢的臺灣同胞船團護航回臺。前前後後與500名乘客同處密閉的機艙,問他當時是否擔心會被感染?他坦言:當然害怕了!擔心傳染給自己,傳染給家人。因為當時在日本「磚石公主號」事件剛剛爆出來,每天感染人數都在增加。「在這個封閉的環境中,我要去接觸武漢籍的同胞,能不怕嗎?怕是正常的。怕,是告訴我們要集中我們的注意力,啟動我們的潛力。同時這也是責任所在,醫生就是救死扶傷。怕歸怕,認清了‘新冠’,你便會覺得這個病毒是可防可控的。但我知道:風險時,要保護好自己。比如口罩是堅決不能摘下來的。」 除了做好自身防護外,夏寒松至始至終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乘務員和乘客的安危。

左圖:夏醫生給機組人員講解防護知識。 右圖:夏醫生與武漢籍乘客在一起
覺察壓力,調整認知
除了是一名醫生外,夏寒松還是一名心理諮商師。「如何更專業,讓自己平靜下來,這是我們出征的一個目的。如果自己亂了陣腳,那是沒辦法去保護別人,更沒辦法工作。所以首先是要對自己進行心理調適。我採取的辦法有:調整呼吸、肌肉放鬆,目的就是使自己平靜下來。」
接下來,他舉了自己隨專機接送滯留在新加坡的武漢籍遊客的例子。雖然整件事已過去了有段日子,但回想起當時的情境,仍讓他感觸良多:從新加坡接回武漢籍遊客,飛機降落武漢機場,很考驗人的心理承受力。飛機晚上6點飛抵武漢,10點半全部乘客下完。飛機上當時乘客147人,我們總共花費了4個半小時。為什麼要花這麼長時間?因為要一個人一個人地檢查,一次只能下6個人。當時的情況是大人小孩又累又餓,焦慮不安。在夏寒松看來,人,越是焦急,越是難受,越是難受,越是焦急,這是一個惡循環。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除錯好自己,讓自己平靜,成為關鍵。「除此之外,我還要照顧好飛機上的人員。比如,有小孩子焦慮,走到我身邊,我會耐心地告訴他:我們中如有一個人一旦出事,大家都走不了。所以要慢慢等……
他認為,「鼓勵」很重要:哪怕是一個小的動作。比如當機組人員從我身邊走過,我就說一聲「辛苦了」!她就很高興,很舒服,因為工作得到了身份鑑定,她會有種榮譽感。還有就是我是醫生,我當時手裏拿著一瓶酒精凝膠,時不時會給乘務員手上噴一點,同時告訴她們:注意手的衛生。這時候對方就會有一種安全感。過一會她們就會又過來,我就再給她們手上噴點。「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有一種安全感,一種被尊重的感覺:認為自己做這份工作是有意義的。而且是有朋友的,這是一種社交的需要。另外就是目光的交流。」夏寒松總結道。殊不知做這些的時候,夏寒松並不輕鬆:穿著防護衣,戴著尿不溼已長達13個小時。「我們是凌晨3點半出發,浦東機場室外溫度當時是4度,後來到了新加坡是31度。先冷,後熱的滋味非常難熬。」

左圖:夏寒松從浦東機場出發。 右圖:穿防護衣的夏寒松
「福祉」的手,利人利己
夏寒松在疫情發生後能夠三次「臨危受命」,完滿完成「護航」任務,在我看來與他早年在日本留學和工作的經歷不無關係。特別是他在日本讀研時更換專業,從腦外科轉到了醫療福祉,這中間的原委引人深思。按照夏寒松說法是:我想幫助別人,同時也是在幫助自己。
作為一名曾經的腦外科醫生,夏寒松見過太多的生死,正因此,他看待生命亦較之常人另有一番深意。他分享了自己所經歷的一段關於「生死」的往事,也正是因為這件事的觸動,讓他下決心改學了福祉。他說,腦外科比較特殊,一些人一旦上了手術檯,原有的智慧,精明強幹都與之「再見」了。有些人就變成了植物人。病房中有一個30多歲的人,做到很高的職位,大腦出血後人都不認識了。前一個月,有很多人給他送花籃,從病房一直襬到樓道。3個月後,便幾乎沒什麼人再來問了;一年後,便沒什麼人來了。雖然人是活下來了,但是生活品質實在是太差了。我的日本指導教授建議我:你應該去學社會福祉。不僅能夠幫到人,而且可以幫到你自己。等你將來老了,有用。「學習的過程中我發現,醫療到了一定程度,是沒有辦法的。可以把命救回來,但有些是無能為力。如何做到能讓這個人雖然不會走路,但還能夠坐著輪椅到餐廳喫飯,還能在同仁來的時候,打著領帶與他們一起去喝杯咖啡。」

左圖:夏寒松(右一)腦神經外科研修時代 右圖:得到神經外科專家大畑建治教授指導
「隨著我們年齡的增長,或者疾病相害作用,生命有力不從心,比如人到了七八十歲時,就需要一個「手」來幫助你。」在夏寒松看來這個手就是「福祉」的手。
他希望未來更多的留學生可以將目光投入福祉專業。首先,福祉,非常有未來的一個學科。其次,即有理論又有操作的東西。是一個綜合性的學習,要有相關醫療知識,也有很多實際操作技能。光學,如無實際操作,也只是紙上談兵。比如偏癱的人如何能夠坐起來,有科學道理在裏邊的。三是,利人利己的事情。不但可以幫人,還可以幫助你的家人。最後,福祉又是友善的,你要心地善良才能做這件事。
留學生如何緩解焦慮
在夏寒松看來,疫情期,無論是呆在日本的留學生,還是回國的學生,還有暫時無法出去,在等簽證的4月生,出現各種焦慮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但焦慮是可以緩解的。他給出了三點建議。
首先,應有正確的資訊,要聽官方的。正能量、有用的資訊。現在是在發病,但是可控的,比如之前各省市派出的醫療隊已分批從武漢撤回,說明疫情是可控的。另外,便是從認知方面解決。「人的認知是不同的。我建議要聽最強的聲音。中國政府的資訊、日本政府的資訊、WHO的資訊、國家衛檢委的資訊,以最強的資訊為準。各國的防疫模式不同,比如中國疫情嚴重時是嚴格化的,‘一刀切’的,而日本多數時候是以‘呼籲’為主。」
其次,學會利用我麼身邊的資源,心理學上稱為「社會性支持」。比如同學們感到焦慮時,你可以與你信任的人商量。可以與父母、當地華人組織,千萬不能「鑽牛角尖」。
最後,焦慮是可以自我調節的。比如通過腹式呼吸、冥想等。通過這些方法焦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緩解。
留學生在中日共同抗「疫」中獲得成長
採訪中,夏寒松對於中日兩國共同抗「疫」給予了積極評價。「這次的中日共同抗擊疫情,體現了兩國一衣帶水的共同命運,中國疫情嚴重的2月初,得到了日本捐贈的大量口罩防護衣等抗」疫「物質;日本疫情開始緊張的今天,中國也為日本分享抗」疫」經驗,捐贈抗「疫」物質,唱響的是兩國從古到今的互幫互助的友好旋律。留學生可以從中獲得成長。」說這番話時,夏寒松很激動:其實,中日兩國民間還是有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的。
順著話題,他回顧了自己早年大學6年學習生涯中,日本人所提供的無私幫助:我本科就讀的白求恩醫科大學與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是姊妹學校。那個年代在國内用日語學醫沒有這方面的專業教材。當時從日本向中國寄東西郵費很貴。東北大學的老師就利用暑假,讓他們的學生坐船到大連,將我們學習的原版教材從日本「人肉」帶過來,坐船因為可以帶很多東西。 「我本科6年就是用這種方式用日語將醫學學完的。」

左圖:白求恩醫科大學醫學系日語醫學專業,得到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田邊教授授課
右圖:公派日本留學時代
10年日本留學和工作最大的收穫
疫情,也讓中國部分家長改變初衷,比如今後不考慮將孩子送出國留學。對此夏寒松並不贊同,他認為疫情只是暫時的,人類最終是一定能夠戰勝它的。因為出國風險就放棄留學,其想法是不理性的,有點因噎廢食:全球化下,留學具有特殊的意義。對於孩子汲取多元文化,開拓視野,可獲得「包容性成長」。「我在日本讀書和工作期間,得到了許多日本有人的照顧和指導。特別是從日本醫生和大學老師那裏學到了‘恕り’(體諒,為他人著想)。無論我是作為一名醫生,還是一名普通人,這點都讓我終生受用。沒有日本留學和工作的那段經歷,我不可能做今天這份工作。」疫情當下,夏寒松認為最好的兩劑良藥就是:感恩和知足。

左圖:與授課教授 藤田弘子(生活科學部人類福祉學)
右圖:留學期間參加外國人日語辯論大會
供稿:陳小牧
圖片:夏寒松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