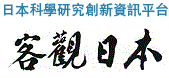和眾多莘莘學子一樣,在那個炎熱的夏天,我經歷了高考。就在考場外等候的爸爸手裏,被塞進來一張傳單。無聊之餘爸爸就那麼瞟了一眼。是的,一定是上天讓這個蒙古男人在那個就算是一動不動也都冒汗的七月裏,看了一眼那張紙。那是一張很普通的傳單,一所留學仲介的介紹。第一天的考試結束回到家,雖然已是夕陽西下的傍晚,但頭頂上彷彿還在冒著熱氣,留著餘熱也不知道是酷暑的原因還是心裏的緊張。或許是為了安撫我的情緒,爸爸還特意裝作輕鬆地說到:「沒事兒,咱們如果考不上心儀的大學,也可以出國留學嘛」。順手甩了甩已經被手汗弄溼稍微有些褶皺的粉色傳單,爽朗地大笑起來。
我家是一個沒有金山銀山也沒有礦山的很普通的家庭,媽媽是人民教師,爸爸比較有遠見地「買斷工齡」之後,做起了生意。所以在當時我也深知,這句留學的話不過是份安慰,所以也就沒有接這個話茬,或許是出於年少時的矜持和懂事。高考結束後,我也就很快地忘了這句話,畢竟人腦對於期待值較低的事情抹去得還是很有效率的。
一天,經過父母房間時隱隱聽到倆人的談話。貌似在拿著存摺算錢。幾個星期前的「留學」一詞又以光速迴歸了我的大腦皮層。已然記不清前後的梗概,但這件事情就悄然地被提上了日程,爸媽也開始試著向親朋好友借錢並仔細地估算著。我這才有了點難不成我要去留學了的實感。對於我來講,一個出生在内蒙古高原小城鎮的高中畢業生,連北京都沒去過,以至於外國一詞遙遠到超出了想像,所以並沒有什麼情緒上的大波動。
又過了幾天,一個人看家的下午,座機響了。是北京某某大學的來電。 是的,高考分數出來後我被錄取了。一所還算可以的大學。那年夏天發大水,很多地區受災後交通被阻斷,所以大學方提前打電話術過來諮詢情況,問一問能不能按時來學校報導。
「我要出國留學了,大學就不去了,謝謝」 。
我默默地看著把麥克風放回座機的右手,足足十秒鐘,不確定剛才的話是出自我的口中。周圍安靜得出奇,連知了叫聲都沒有。
貧草原的夏天很短暫,泛黃的草原有了一絲成熟的韻味。雖然還有殘夏的溫暖,但吹過的風卻是清爽怡人。猶如我扔掉好幾十公斤的高中課本後的心情一樣。

夏末的内蒙古貧草原 也很是愜意。花兒點點,自在地與藍天白雲嘮著日常
九月份,就去了内蒙的首府呼和浩特學習日語順便辦理手續。綠皮火車的硬座,30多個小時也沒覺得有多漫長。同一趟列車上遇見了去上大學的高中同學。同一個方向,不同的目的。孰對孰錯,那時的我也無法判斷。天黑了白,白了黑。伴隨著我忐忑的心情火車徐徐地駛進了這個別名為「青城」的城市。

現在去呼和浩特可以坐飛機了,圖為呼和浩特機場外觀
在一所專門學習日語的留學機構,有很多年齡層不一樣的學生。但都是為了去日本留學這個目標聚在了一起。我記得很清楚,那天穿了一套牛仔裙,緊湊的剪裁和我的心情一樣美好。因為入學手續耽誤了一點時間,進入教室的時候已經開始上課了。老師指了一個空艙,我也趕緊坐了下來。用幾秒鐘整理了不安的情緒後將堅定的目光移向了黑板。人生第一次見到了日語的平假名,聽到了「あ い う え お…」的發音。
我所在的班級一共有兩名日語老師。都是中年「海龜」。分別教日語文法和口語。除了緊張的學習,老師經常會穿插一些自己當年留學時候的小故事來活躍課堂氣氛。每次都是聽得津津有味,伴隨著無限的憧憬。有一天女老師講到自己留學期間,在一所高爾夫球場打工。當時只有在電視裏見過高爾夫的我自然是聽得很仔細。老師繼續講到,她開著高爾夫球場的電瓶車載著兩名客人,「馳騁」在蜿蜒崎嶇凹凸不平的球場居然翻車讓兩位客人摔了個腳朝天。老師用不算流利的日語一直道歉……。說不清自己為什麼對這件小趣事留有如此深的印象,甚至忘記了下面的結尾是什麼。還有記憶猶新的就是老師說當時日本最紅的明星叫濱崎步,至今這名女歌后還在以傳奇式的人生為娛記貢獻著很多新聞。
北方冬天的冷總是超乎你的想像。在辦理出國手續和努力學習日語的日子裏,掛曆的紙張也變得單薄,隻剩下了最後一張。我也生平第一次在外面的公用電話亭給爸媽打電話術的時候把一隻耳朵凍了。就在白雪皚皚的一月,完成了為期四個月的學日語歷程,回到了老家準備留學前的事宜。
在準備一厚沓的資料的同時,日方的入學通知書也如願地來到了我的手中(日本是四月份開學)。接下來就是辦理簽證最後一個關卡。少數民族地區的内蒙是要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辦理。於是在媽媽的陪同下我開啟了生平的第二次北京之旅。之所以說是第二次,其實是因為之前為了參加日本語言學校的考試,仲介公司的老師領我去了一趟北京。早上到達,在駐北京辦事處參加完筆試和麪試之後乘坐晚上的火車又回去了。一路風塵僕僕,精神上和精力上都沒有餘力好好看看首都的面貌。而這次不同,我的心情很是激動,過了懷柔得知下一站就是終點站北京站之後,我就一直盯著窗外,甚至吝惜眨眼的那幾毫秒。「這就是北京,這就是首都」!小心翼翼地掩護著心裏的雀躍,最後的傲嬌和虛榮心在把持著自己,像端著滿滿一杯水時的那種小心,不想讓別人看出我沒「見過大世面」。

很懷念的綠皮火車
一路輾轉來到了目的地——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在南銀大廈裏我也是第一次感受了電梯,整個人暈乎乎的像是飄在白雲之上。恍惚中彷彿自己走進了多啦a夢的空間時間之門。一直到現在我都在心裏把那扇電梯門叫做「命運之門」。雖然一切未知,但是十八歲的我,勇敢地踏出了那一步直到現在這條路還在延伸。
一首夢然的原創《少年》之前火遍了大江南北。就像歌詞裏面寫的一樣「路在腳下,其實並不複雜。我還是從前那個少年,沒有一絲絲改變。時間隻不過是考驗,種在心中信念絲毫未減。眼前這個少年,還是最初那張臉,面前再多艱險也不退卻」。
少年,不是一個階段,而是一顆心。
供稿:安寧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