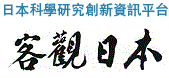上接: 我的日本留學路(一):放棄北京某大學,突擊日語拿簽證
那是17年前乍暖還寒的三月,正處豆蔻年華的我在媽媽的陪伴下,從内蒙的一個小城市乘坐綠皮火車來到了首都北京。是的,經過多方努力和籌備,我留學去日本的事情終於有了眉目,接到日方寄過來的入學通知書的時候,終於對這件事有了真實感。很輕很薄的一張紙,放在手心裏卻感覺很沉很沉,欣喜地讀了好幾遍,那個紅彤彤的印章在太陽的照耀下格外耀眼。

這是我多年後再次乘坐的綠皮車
當然光有入學通知書和邀請函是不夠的,最讓人緊張的不外乎是簽證。這幾個月所有努力辦理的資料都要提交給日本大使館,最終使館根據材料來判斷是否簽發去日本留學的「入門證」。
出發前的晚上,我鄭重地將確認了不下十遍的資料裝進了一張牛皮信封。對於當時的我來講,牛皮紙袋莫名地有種儀式感,感覺自己像大人一樣在「辦大事」了。
將兩人份的隨行物品放進了一個淺黃色的單肩包,在貼近身體的那側,牛皮信封靜靜地「站在」那裏——我特意豎著放的,怕資料壓出褶皺。現在已記不清是誰送我們去了車站,怎麼上的車,隻記得第二天早上我們在北京西站下了車。我單肩挎著包,跟在媽媽的後面,隨著墮胎一路走到了地鐵站。媽媽應該是在火車上打聽過的吧,腳步雖然很快但是背影看著很從容。之後我們先後輾轉了地鐵和公車,沒記錯的話是在三元橋下的車,來到了北京的日本大使館所在地。
這個被稱作南銀大廈的高樓,在那個初春的中午顯得格外地耀眼。熾熱的太陽將光芒毫無吝嗇地灑在這個滿是玻璃的建築上。在那個年代,周圍的高層建築還是很少的,尤其是站在樓底仰望的時候更顯這座樓的巍峨。

南銀大廈
諮詢了辦事處,得知要分批進入,一次只能進入30人左右。我被分到了下午兩點半的那一組。看了看手錶,還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找個地方等一下吧。環望四周,這才發現樓外面的綠化是很美的,種滿了各種各樣的花,與迎風飄揚的萬國旗交相輝映甚是好看。繞著樓一週,有很多長方形石凳供人休息。選擇了一個背朝高樓面向大街的石凳坐下。將手裏的牛皮信封放在了自己和媽媽的中間,隨後也把背了大半天的單肩揹包放在了上面。稍微舒展了一下筋骨和媽媽對視了一眼,不言而喻地輕鬆。看著街上形形色色的汽車和行人,很多都是叫不上牌子的。在我十點鐘的方位有一個公車站點,有很多貌似打工族的年輕人在排隊。巴士來一趟拉走一群,幾分鐘後又排了很多人。不知道看了多少趟公車來了去,去了來。不經意間看向媽媽,在太陽的炙烤下她的額頭沁出了些許的汗珠。
雖然我和媽媽是那種亦師亦友的關係,但在那個敏感的年齡段我很少會說出關心媽媽的話。與絕大多數處在青春期折騰的同齡人一樣,總是有種「愛你在心口難開」的固執和傲嬌。現在想想估計是覺得自己馬上要出國了,不能待在媽媽身邊的一股情愫作祟吧,我建議媽媽去那個公車站點的椅子上坐坐,因為那裏可以暫時躲避太陽公公那得意而耀眼的「笑」。目測距離也就二十米。媽媽答應了,我們起身來到了公車站點亭下的陰涼處。頓時身上的燥熱平復了許多。正在得意讓媽媽遠離了「受罪」的我,被媽媽的一句話驚醒:
「信封你拿著呢嗎?」
「你沒拿嗎?」我聲音開發端抖,然後本能地回頭望向幾分鐘前我們還坐著的石凳,光滑的石凳上空無一物。此時此刻我多希望一向引以為傲的2.0的視力是假的,讓我看得不是那麼的清晰,一眼就看見那個信封不在石凳上。一定是剛才起身的時候我隻拿了包卻遺忘了在其底下的信封。
雖然是很近的距離,我拼盡全力跑了回去生怕再晚一秒鐘信封就會離我們更遠。然而現實並沒有讓我們的故事發生轉折。旁邊的石凳上坐著一位男士低頭在看書,儘量不想打攪他午後閱讀的美好氛圍,努力抑制自己焦急的心情問道:「先生,您有看到這個石凳上的一個牛皮信封嗎?」 他搖了搖頭。之後又問了好幾組周圍的人,都說沒有看見。只有一個人說好像有一位男士在我們離開之後坐下了,在看一個信封隨後便走掉了......
「謝...」,另一個謝字已經消失在我飛奔的途中。
大腦完全是懵的狀態。記不清自己繞著南銀大廈跑了多少圈,問了多少個人。那種感覺很奇怪也很不舒服。大腦已經罷工像是在刻意逃避這件不該發生的事情,跟人說話時自己聽著都有迴響。也問了大樓訊息處,一個年輕的小姐姐用對講機幫我跟所有的工作人員問有沒有人撿到信封的時候,等候回信的那十秒鐘我幻想了無數次聽到肯定的答案。但結局是,謝過一臉抱歉和擔憂的小姐姐,繼續跑……
當我再次跑到南銀大廈入口處時,已經有二三十個人排隊,按照保安的指示緩緩進入。是的,如果沒出這個意外,我也應該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看了一眼手錶,兩點三十分。本以為我會掉眼淚,結果一滴也沒流,一定是太陽烤的再加上一直跑導致身體裏的水分都被榨乾了吧。
很無助很無助,媽媽也在周圍樹木叢中仔細地找著,看到稍微有茶色的東西都會反射性地用視線掃一下。媽媽心臟不是很好,我真的怕她在這裏倒下。漸漸感覺到了兩個人力量的侷限性,我在路邊的公用電話亭聯繫了在北京認識的唯一一個高中同學。一個多小時後朋友從大學校園風塵僕僕地趕到,手裏攥著一厚沓「尋物啟事」和一卷膠帶。一定是恐慌值過大將腦内的感情中樞短路了,以致於忘了說聲謝謝,就爭分奪秒地開始在周圍張貼並打聽消息。

南銀大廈綠帶(圖片取自網路)
不知不覺天也暗了下來,能見度變得很低。三個人一下午連口水也沒喝。一無所獲地又聚在了南銀大廈的樓底。在還算「頭腦清醒」的朋友的建議下我們選擇了警報。人生第一次坐了警車,還是朝陽區派出所的。警察首先安撫了我們的情緒,但是又很委婉道地出:「雖然知道你們很著急,但是如果是自己弄丟的東西是不能立案的。你們只能備案登記一下,如果有好心人撿到了會通知你們的」。雖然警察叔叔極力溫柔地表達著,但一字一句,還是硬生生地將剛剛浮現的希望 「扼殺」在了水面下。
走出朝陽區派出所,晚上六點的北京已是萬家燈火。突然感覺北京好大好陌生。身體的疲憊加上精神上的打擊,已經完全邁不動步子了。朋友又很貼心地打聽到,就在派出所的旁邊,有個地下室旅店,花了20還是40元訂了一間房。躺在牀上,隱約能聽到媽媽自責的哭泣聲。我依舊沒有眼淚,兩眼放空就那麼躺著,沒有開燈也看不到天花板,但我彷彿能看見那個我檢查了不下十遍的牛皮信封……

日本小學館(出版社)大樓前的多啦a夢(照片:客觀日本編輯部)
如果真的有多啦a夢的時間機器,我挺想橫越回去看看當時的自己,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刻的自己,是狼狽還是堅強,亦或是有了更多的領悟。我要不要抱一抱那個精疲力盡地站在南銀大廈樓底的她,要不要拍拍那個望著地下室的天花板卻哭不出來的她。打住!最重要的提醒她起身之前不要忘記牛皮信封才對。
第二天以後發生的事情,我會在下一篇連載裏和大家分享。
供稿:安寧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