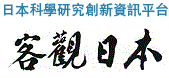體內的生物鐘告訴我,應該是早上了。
雖然徹夜難眠,但還是看了看錶,昏暗中使勁張大眼睛,已經六點了。本以為一切都是夢,但是陌生的天花板告訴我這裏不是我的家。環望四周,媽媽躺在對面的牀上。雪白的牀單和被罩提醒我這裏是旅店。
其實也沒花多長時間,一切記憶又湧回了大腦。
是的,在這鋪牀榻上,我捱過了17年來最難過的一晚。昨天在日本大使館的樓下,等候辦理簽證的時候把所有資料都弄丟的場景歷歷在目。側目看了看媽媽,想必也是一夜沒睡吧。本想說些什麼的,可是乾裂的嘴脣讓我感覺到了一絲絲扯痛。痛感是很現實的,又一次將這不是夢的事實,用一種很直接的方式通過神經報告給了大腦。沒喫沒喝到現在,奇怪的是絲毫感覺不到餓意。
媽媽也已經坐起來開始整理東西,地下室的燈光,不是很亮。隱約能看得到媽媽紅腫的雙眼。
「媽,餓不餓?」我的聲音低到自己都有點聽不到。空氣中瀰漫著我懊悔和抱歉的情緒。
媽媽也只是搖了搖頭。示意我去叫我的同學,說人家一直跟著幫忙找東西,怎麼也要請人家喫早餐。
走出地下室,天亮了。三個人在「地上」匯合。商量去哪裏喫早餐。已經有12個小空間時間腹了,胃袋居然沒有跟我示威它現在的「貧瘠狀態」。
「走吧,喫完飯去火車站看看能不能買到回去的票」。媽媽邊說邊往外走。我又一次背上了我的黃色單肩包,出奇地沉,宛如我跌倒谷底的心情一樣。
沒走兩步,朋友的BP機響了。我沒多加想,腳步緊隨著媽媽。可能是因為在地下室的關係,旅店裏一直沒有信號,消息這時候才傳來吧。

傳呼機和公用電話亭(圖片源於網路)
「這是不是你家的座機號?」身後傳來朋友的聲音。看著這一串熟悉的數字,估計爸爸也是在家裏擔心了一個晚上吧。丟完資料後跟爸爸聯繫之後,在派出所報完案後也忘記給他打電話術了。當年,公用電話亭的普及率還是很高的。沿著馬路走了十幾米,就有一個。跟朋友借了IC電話術卡,我撥通家裏的電話術。爸爸的聲音依舊那麼地深沉且有包容力。還沒等我把昨天的始末講出口,爸爸就急切地問我有沒有筆和紙,讓我記一串號碼。一邊擔心長途電話術會不會將電話術卡里的錢都耗盡,一邊手忙腳亂地翻出筆和紙記了下來。
「我從昨天半夜就開始給你同學打傳呼(BP call)」爸爸說。
是的,我和我媽那時候也沒有手機。
「一直也沒回信,就等到現在」。爸爸繼續說道。
「我們住了個旅店,是地下的那種,估計是沒有信號吧」。讓您擔心了,在心裏默默補了後面一句。
「昨天晚上快十二點的時候,有個人給咱家打電話術,問是不是安寧的家。說是撿到了你丟的資料。」爸爸幾乎是不喘氣地說完後又接到:「說是先給你日本學校駐北京辦事處打了電話術,但是都已經下班了。然後翻看裏面的材料才找到咱家的電話術號碼。」聽著聽著我明顯感覺到我握著聽筒的手有點發抖,甚至從昨晚持續到現在的頭痛在那麼幾秒鐘之内神奇般地消失了。那種滋味我自己覺得絕對應該是與孫悟空拿掉緊箍咒後的感受是等同的。
這時媽媽也湊了過來,應該是擔心發生了什麼事吧,但我來不及解釋,雖然我很想很想大聲地叫出來。但為了仔細把爸爸的話聽完而忍住了。
「剛才那個號碼,是撿到的那個人的BP機號碼,你聯繫他一下吧。然後,好好照顧你媽」。在爸爸簡單的幾聲叮囑之後,我掛斷了電話術,望向媽媽。她用眼神示意我趕快告訴她到底發生了什麼。我用明顯提升了一個八度的聲音,將有人撿到我的證件的事情跟媽媽和朋友講了一遍,一口氣下來,我差點窒息。
就在同一個電話術亭我撥打了對方的傳呼號。接通後,我將自己的姓名和留言轉告給了接線員。幾乎祈禱式地放回麥克風。站在一步之遙的距離等對方打回來。(不太懂BP機用法的朋友請自行詢問)
三個人六隻眼,眨呀眨,有默契地屏息等候,彷彿整個世界都靜止了。馬路上的吵嚷聲都被我們用意念自動降噪生怕聽不到來電的鈴聲。
「鈴……」
反射性地將朋友推到電話機的前面。自己實在不敢去接。朋友也是反射性地拿起了聽筒,生怕下一秒鈴聲就會斷掉一樣。有那麼一世紀之久的感覺,朋友談話結束轉過來跟我們說:「是個男的,說在一個叫做肖村的地方。讓我們到XX家俱城前面下車後再聯繫他。」
「他還說什麼了嗎?」媽媽急切地問道。
「就問了你們一共幾個人之類的。還問我是本人嗎?」朋友回答到。
站在一旁的我很明顯地聽到了一聲來自自己肚子「咕……」的動靜,而且是那種不受控制的接二連三的咕咕叫。瞬間不知道為什麼,好餓!
還是辦正事要緊,我們決定先去拿資料後再喫飯。媽媽沒有絲毫猶豫,抬手召喚了計程車。在我們那個小城市,只要不出市外,打車資均為五元,北京的物價其實對於當時的我們來講是有些貴的。然而看到這麼果斷的媽媽,莫名感覺她的背影又高又大。
司機是個很和善的人,用道地的北京腔寒暄著問我們從何而來要辦何事。媽媽坐在副駕駛座跟他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我肚子的咕咕叫也一直沒有停,附和著司機爽朗的笑聲充滿了車内。應該是媽媽跟他說了我們的「遭遇」吧。司機先生也是很直快地說道:「也有可能會跟你們要一些好處費,這都沒準兒」。媽媽也附和著說:「是呢。不過要多少錢我都要給啊,沒辦法。能找回來就已經阿彌陀佛了」。我和朋友對視了一眼,畢竟對於還沒走上社會的我們來講,一聽到有關錢的事情還是會很緊張和有壓力的。
伴隨著司機先生的一句「就這兒了,到了您吶」。我望向車窗外。這裏應該是正在開發的地段,空曠但又很整潔。工地用的沙子在遠處堆成了好幾個大壩式的「山地」。我和朋友在周圍尋找公用電話亭。偶然間瞥了一眼媽媽,看見她偷偷地數著腰包裏的現金。應該只有那麼0.1秒的時間,我的眼淚擠滿了眼眶,脹得有點痠痛。她一定是在數剩餘的錢有多少,計算著要給對方多少謝禮,又留多少錢買回程的火車票。在我努力控制情緒的時候,朋友已經駕輕就熟地撥通了對方的傳呼號告知我們已經到了。
大概等了五分鐘左右的時間,就看見遠處沙子壩上的三個人影。雖然有點遠,但是不難看出他們是在一邊走一邊喫。鬆軟的沙地讓他們的步伐有些踉蹌。我心裏想:之前問我們一共幾個人所以你們也是三個人過來的呀!這是要談判的架勢啊!
距離稍微近了之後,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得到我那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牛皮信封了。被夾在領頭的人的右臂裏,左手拿著熱乎乎的包子在喫。身後的兩個人也是一人拿了一個塑膠袋裏面裝著類似的早餐,三個人均穿著工地工人的服裝。應該就是他們了。我一個箭步迎了上去。剛走到「壩下」,他們已經到達了「壩頂」了。已經能聞得到他們包子的香氣了。
「你叫安寧嗎?」對方先開了口。
「是的,您好。聽說您撿到了我丟失的材料,謝謝您」。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著。
「你爸媽讓你出國真不容易呢,以後要多注意點,不要再丟東西了。」對方又說到: 「你看看這裏有沒有缺什麼證件」。隨後把牛皮信封遞了過來。因為地勢的關係,我是屬於仰望著他的姿勢。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柔和的陽光並不是那麼刺眼,從他的背後照射過來,彷彿他站在一個光圈裏。一瞬間,有點佛祖下凡來教訓我這個毛躁小屁孩的感覺。
雙手接過稍微沾了點油漬的牛皮信封。但還是平整的。媽媽在一旁忙著感謝,我則是有些激動地查看信封裏的證件以及材料。完好無損,都在! 翻開護照,一個豆蔻年華的小女生在朝我微笑,彷彿在跟我說「我回來咯」。

媽媽很用力地想塞給他一些錢,但是對方也一直拒絕,說「大姐,真的沒有關係的,你們供一個留學生不容易,心領了」。那時那刻,那一幕,雖然自己是整個事件的主角,但又彷彿站在圈外看了一場電影。
初春的陽光和煦而溫暖。媽媽擦了擦額頭沁出的少許汗水,領著我們又一次鞠躬道謝。隨後我們便離開了那個逗留了不到二十分鐘的地方。
回程的路上,媽媽開玩笑說一夜之間長了好幾根白頭髮,讓我負責。我說:「好!回去以後給你買黑芝麻……」。
媽媽開懷大笑,沒覺得我的回答有多麼幽默,隻記得媽媽笑了好久,好久……(未完待續)
供稿:安寧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