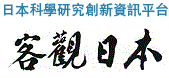隨著公車有節奏的顛簸,我的嘴角也一直保持著上揚的角度,猶如我雲破天開的心情。
途中好幾次不禁伸出手摸了摸肩上的黃色揹包。隔著一層布,似乎都能感受到那個失而復得的牛皮信封的溫度。心裏默默地說了聲:「謝謝你沒有走遠」。與鄰座的媽媽有默契地相視一笑,我又將臉朝向了窗外,任由正午的陽光灑滿全身。
十幾分鐘前,在一個叫做肖村的地方,我們謝別了那位,拾到我丟失的資料的先生。
「阿姨,我們打車來的時候花了三十四元錢,回程也不需要趕時間,不如我們坐公車吧,一人兩元,您覺得呢?」 朋友依舊細心地給出了建議。
媽媽點了點頭同意了乘坐巴士回到北京市内。再次見到公車站,我反射性地抓緊了揹包。失而復得,彌足珍貴。

當年重要的資料都是放在這種牛皮紙袋裏(圖片來自網路)
在終點站的前門車站下了車。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置身於北京的市區。墮胎車輛絡繹不絕,與南銀大廈附近相比更多了一些生活的氣息。已是飢腸轆轆的我們在一家菜館落下腳來,媽媽略顯興奮,一直招呼朋友多點一些菜,席間也是一直將菜盤推向我們倆。我用了很短的時間將一盤餃子都喫光了,不知道是首都的餃子太好喫了還是因為真餓到了一定程度。
隨後向店老闆打聽了一下去三元橋的公車路線。是的,我們決定再次去趟日本大使館辦理申請簽證。與朋友就此別過,除了感謝,彼此眼中多了一份歷經波折後的默契與堅強。透過朋友的瞳孔映襯出的自己,彷彿也是成熟了很多。
幾經輾轉,又一次來到了24小時前曾經來過的地方。一切都不陌生,依然屹立的南銀大廈,依然花草搖曳的四周,依然與藍天白雲交相輝映的萬國旗,還有我們曾經將牛皮信封弄丟的那墩石凳。我刻意地將媽媽「安頓」在之前我們坐過的那張石凳上,既然時間不能倒流,那就讓我從最初的環節來彌補一下吧。
我一個人去領取排隊進入的號碼牌。同樣的時間,同樣的路,同樣的人。不同的心情不同的世界。我很認真地走著每一步,體會著本應該昨天就會經歷的這段間距。有那麼一瞬間,淚水幾乎就流了出來。迅速地仰起了頭,透過覆蓋在眼部玻璃體上的淚水,屈光折射出的藍天顯得更深邃。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初春的空氣穿過鼻腔,沁入肺部然拂遍了全身的細胞,好舒服。 24小時前,那個為尋找丟失的資料而跑到體力透支,雙手杵著膝蓋看著地面氣喘吁吁的女孩,今天懷著感恩的心情感受著失而復得的美好。
回到了媽媽身邊,媽媽還半開玩笑地說:「今天無論怎麼曬,我都不去公車站點避太陽了」。隨後我們母女倆哈哈大笑了起來。
終於到了指定的時間。我隨著墮胎走到了入口等候區。同一批的有二十個人左右,年齡層雖然各有不同,臉上卻有著多多少少相同的緊張感。有幾位中年人,從容地交談著,想必不是第一次來辦簽證吧。我延伸了耳朵希望能從他們的談話中得到一些對辦理簽證有幫助的消息。
工作人員將我們領進了一個房間,一人發了一張表格交代了幾句之後就出去了。白紙黑字用中日兩國語言寫著簽證申請表幾個大字。本來就緊張的心情又加重了幾分。屋内分散擺放著幾張長方形的桌子,大家找好最佳位置後站著埋頭填表。

當時沒有相機,不能隨時拍照,此圖為示意圖(圖片來自網路)
再三檢查了自己填完的表格之後,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等候之餘觀察起了四周。在二十多個人的房間,有一位中年女士非常耀眼奪目,穿著也很不一般,雖然達不到兩隻手十枚戒指般誇張,但也全身金光閃閃。看著駕輕就熟的樣子,應該是總出國吧,我徑自想像著。
一個人處在自我價值觀還沒有具體模製的那個年紀,判斷一切事物的基準莫過於直觀的物質表現。所以看到她我的第一直覺就是:她應該很有錢。隨即一股莫名的距離感湧上心頭,雖然當時不知道那個感覺是來自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
媽媽坐在家屬等候區,可能是我的情緒表達讓她看出了一絲不安的情緒吧。她示意我可以讓那位看起來很有經驗的女士「指點迷津」。我瞄了一眼,她已然填完了表格後在等候著,無聊地用手敲著鼓點兒,時而望向門口貌似等候工作人員的到來。
雖然心裏有些許排斥但還是乖乖地聽了媽媽的話湊到了她跟前,莫不過一步之遙的距離。
「阿姨......你好」。我小心翼翼地斟酌著對方的稱呼,有點躊躇地開了口。
「......」對方的眼神飄了過來,確認了一下說話人的方向。
「……」
「叫錯了?」「聲音不夠響亮?」我的腦海迅速地閃過N個問號。2003年的時候還沒有「正妹」、「親」等稱呼,也沒有無論見到多大年紀的女性都叫「姐姐」的萬能稱謂。叫「阿姨」,文法上倫理上和情理上應該沒有錯呀!
「阿姨,我想問一下,填完表格之後就要這麼等著嗎?您能不能幫我看看我填的對不對?」一口氣說出了自己搭訕的初衷,鼓起勇氣抬頭看著她的臉,亦或是想避開她那金光閃閃的一直不耐煩地在桌面上敲鼓點兒的雙手吧。
「不知道!!」
只有在書上見過「鼻孔看人」這個詞語,沒想到這一天有機會親身體驗到了,而且是「被」的這一方。
「哦,謝謝」。伴隨著那個未曾停歇的「鼓點」聲,我默默地退回了原來所站的位置。
在遠處的媽媽看見了我們的「談話過程」,很欣慰的投過來一抹微笑。應該是覺得放心了不少。顯然,她並沒有聽到我們的談話内容。
都怪媽媽非要讓我跟她「諮詢」,有那麼一刻感覺自己受到的「委屈」都是媽媽的錯。但與媽媽那抹無限慈祥的微笑對視之後,瞬間我收起了我的埋怨,內心平靜了好多。媽媽一直是個很熱愛生活的人,她嬌小的身軀充滿了巨大的能量。那種正向的,樂觀的以及大格局的世界觀,就算對於處在叛逆期的我而言,也會讓我自愧和佩服。
被旁邊幾個人的聲音打斷了短暫的負面情緒。跟我一個桌子的是三五個來自新疆的年輕人。雖然現在日本簽證不允許個人去申辦了,但在當時少數民族地區的居民,是需要去駐北京的領事館辦理的。同為少數民族,心底莫名地湧出了一股親切感。看著他們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指著表格像是在討論著什麼。原來是漢語不太好填起表格來似乎有點困難。雖然自己也不知對否,但還是禮貌地詢問了他們需不需要幫忙。就這樣,我幫助他們幾個一起完成了表格的填寫。如若是當今社會,到處在被呼籲尊重和保護個人隱私的這道門檻,恐怕我也是不敢跨越的吧。
再後來,我們依次被叫到窗口,我懷著忐忑的心雙手提交了牛皮信封裏裝有的所有資料與那張有故事的申請表。被告知一週後出結果。
直到現在,每每想起我在辦理簽證的前一個小時,把所有資料都弄丟這件事情,都後怕不已。上一篇連載發表之後,微信裏滑進來媽媽發來的一條語音消息。
「女兒,你讓媽媽又思緒萬千了」。
曾經是一名理科教師的媽媽不禁感性運動了起來。下一秒我撥通了媽媽的電話術號碼。
已經過去18年了,我其實很想知道在那個萬念俱灰,彷徨無助地住在地下室旅館的夜晚,媽媽都想了些什麼。媽媽一直不曾提起。媽媽說她已用一夜之間冒出來的額前白髮「祭奠」了那一晚的絕望,女兒你隻需要熱愛生活,積極向前。
腦科學家茂木健一郎曾說過:「忘卻是世上最好的美容術」。希望我們都忘掉所有的不開心,善待生活,善待自我……(未完待續)
供稿:安寧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