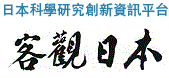回到了内蒙老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將所發生的事情講給了爸爸和姐姐們聽。
爸爸就那麼聽著,沒有多說一句話。強壯的蒙古漢子抿著嘴,耐心地看著我一直講,一直講。雖然沒有過多的情緒表達,但很明顯的,眼睛一直彎彎著,弧度很美,充滿了欣慰。
彷彿卸下了千斤重的鎧甲,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三夜。
身處陌生的城市,尤其是首都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沒有了父母在前面的遮擋,獨自去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潛意識裏會給羽翼未豐的身軀披上鋼鐵鎧甲。並不是畏縮,只是想讓自己看起來更堅強一些罷了。只有回到了安全的港灣,才會如釋重負。
三姐看著睡眼惺忪的我開玩笑地說:「你再不起來,都趕不上開學的日子了。」
很多朋友應該知道,日本的新學年的開始是四月份,異於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話說大和民族對櫻花別有鐘情。恰巧櫻花的開花季是三月末至四月初。在唯美的櫻花雨下緬懷傷感的畢業季,在花海爛漫的季節迎來入學式想必是也別有風情,亦是一輩子的回憶。

是的,我當初也是這麼想的。翻查資料後才發現,在很早之前日本也是九月份入學的教育體制。到了明治19年,也就是1886年的時候,因為國家一年的年終決算會在三到四月份舉行,所以為了配合國家的整體預算統計,以及國家發放教育基金的時期,以高等師範院校為首,將新學期的初始改到了四月份。之後慢慢擴展到其他師範院校以及小學。進入大正時期後實現了全國上下的統一直至現在。
「爸媽交給了我一項很重要的任務」。
三姐攥著一沓紅色的紙張,很得意地走了過來。
我慵懶地看了一眼三姐,與她的精神面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隨之眼神定格在了她手上攥著的鈔票上。
「爸媽說今天讓我陪你去買衣服」,姐姐也沒等我問她,徑自地說了出來。
我是家裏四姐妹中最小的,從小穿衣服「撿剩」的機率很大,家庭條件雖然沒有到拮据的程度,但由於身為教育工作者的媽媽比較嚴苛,所以還真是除了最低限度的衣物之外,從沒有這麼「奢侈」的買衣服的機會。欣喜若狂,亦或是受寵若驚,是屬於那個年紀的高興。
心裏的某個角落雖然還介意著那沒交齊的18萬日元的學費,但短暫地安慰了一下自己,小心翼翼地收起過意不去的心理,騎著腳踏車出發了。我坐在姐姐的後座位,上坡的時候會下來幫她推一下,等到了平坦的大道,我又小跑追上去,看準時機一蹬一跳,穩穩地坐上去。
三姐和我的年齡差最小,總有說不完的話,挨批評之後會一起「抱怨」爸爸媽媽,也會聊一些那個年紀該聊的話題。不一會的功夫就來到了市中心的主打年輕女孩服裝的商場。
聽說東京的冬天不是很冷。氣溫也不會低於0度,所以除了厚重衣服,其他季節的衣服各買了一套,短袖和牛仔衣褲多買了一些。看著三姐認真地幫我搭配選擇,努力地和店老闆討價還價。我的思緒不禁飛回到幾年前的一幕,還是小學生的我們,總是去附近的個人商店買零食喫。每次都是我進去買。有時候我讓她進去,她總是讓我在外面等著。姐姐從小讀的蒙古族學校,所以漢語不是很好,可能是出於不好意思吧,不想讓我聽到她講漢語……
拎著大包小包打道回府。姐姐將剩下的錢還給了爸爸,爸爸也沒有問太多細節,從另一間屋子裏拽出來一個大大的行李箱。原來是兵分兩路,爸爸媽媽出去買行李箱去了。那個行李箱很大,大的很離譜。因為據說留學生可以帶30公斤重的箱子,所以特意買了較大的。把所有衣服放進去之後還有很大的空間。媽媽不知道從哪兒變出了一牀新的被子和枕頭,與牀單被罩一起整整齊齊鋪在了最底層。
行李箱日漸被填滿,也到了我該出發的日子。身著一套新買的衣服,我握著火車票與爸爸媽媽在候車室裏與親人們告別。爸爸這次為了送我到北京,也是忙乎了許多個日夜才把手頭上的事情安頓好。
熟悉的綠皮火車,熟悉的硬座……再見了家鄉,再見了親人。

在北京辦好了入住手續,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備最後階段的事宜。
爸爸站起身來,從腰間解下一個類似腰包的東西,走到我身邊:「這裏的三萬塊錢用來換日元,有家仲介公司說可以到他們那裏兌換日元。」爸爸一邊說,一邊很有儀式感地把腰包系在了我的身上。將腰帶的帶子縮了又縮,直到緊緊地環住了我的腰身。
「你和同學一起去吧,爸爸媽媽留在旅店裏喝茶」。爸爸雲淡風輕地說了一句。但對於我,瞬間感覺那個腰間沉重了許多。但是爸爸投過來的眼神,掌心傳到我肩膀的溫度都表達了他的確定。
我無比自信地點了點頭:「保證完成任務!」第一次拿到這麼多錢的我,內心既是興奮又有些許惶恐,更多的是有一種要做給爸媽看看,今後我自己啥事情都能應付的衝動。其實,如果放到現在,自己一定會去求證仲介公司是否有兌換外幣資質,會使用銀行等更加正規的渠道來兌換,但在當時,真是一絲絲這種疑念都沒有——正如老話所說的那樣,經歷的事情多了,才能成長。
跟著同學,一路輾轉來到一處金融氣息很濃的商業街,高樓林立,建築物也多是現代風格。按照位址來到了一幢很美的辦公大樓下,過程很順利,一位中年男子接待了我們。面容和藹,身體略有發福。流程式數著人民幣,計算好匯率之後熟練地將日元交給了我們。
一共換了35萬日元。與所剩無幾的人民幣一起慎重地放進腰包裏。三十五張一萬日元的鈔票,相比之前的人民幣,薄了很多。這種數字後面好幾個零的面額鈔票還是頭一次見到。與同學互看了一眼,對方也是一片茫然。

日元紙幣最大面額為一萬
之後又去取機票,在還未流行電子機票的年代,需要面對面地換取。穿梭於地鐵和巴士中,拿回機票上的日期告訴我,還有不到24小時的時間,我就要離開了。即將出國的感覺慢慢變得具象化,忐忑和興奮交錯,五味雜陳。
晚飯後,把追加購買的東西都裝好,蓋上行李箱後長長地舒了口氣。臨時找不到稱重器,於是推著巨大的行李箱來到了前門小喫街。人山人海,好不熱鬧。那時候大小城市中,「量身高量體重」可謂是鬧市中的一道風景線。 花了兩角錢,確認之後也算安心了。
多少有些緊張,而且晚上輾轉反側的不止我一個人。
首都機場的門口,來來往往的人群。計程車停了又走,走了又來。我們也從其中的一輛中下來,拽著行李箱走進了所謂的祖國的「玄関口」。留下一個雙肩揹包,看著那隻大大的皮箱「上」了傳送帶,在美麗空姐的一鍵操控下,遠離了我的視線拐彎後消失了。
第一次乘坐飛機,反而沒有不安,因為也不知道是何等感覺。
與爸爸媽媽微笑著告別,沒有上演淚目的戲碼,也沒有不捨的橋段。我清晰地記得,自己過完安檢之後,那種昂首挺胸的狀態,很自豪也很自信。特意沒有回頭看爸爸媽媽,那是自己最後的防線,因為我知道,回了頭,淚就會決堤。
媽媽經常說「出門在外要多問,自己不要瞎闖」。於是每遇見一位保安人員我都指著登機證上的數字問一下走的對不對。
從這裏開始,每走一步,都是未知的領域,與此同時也是新鮮和刺激的。
日語裏有句諺語叫做「可愛い子には旅をさせよ」,中文譯為「愛子女需令其經風雨」。做這個決定很難,過程更為辛苦。但是一旦選擇走下去,相信風雨過後就會有彩虹。
前一晚的睡眠不足加上早起,登機後的我已是精疲力盡。緊繃的神經最終沒有敵過周公的誘惑,飛機起飛前就已經靠著窗戶睡著了。人生第一次離開地面的體驗也就在睡夢中度過了。直到被空氣中的飯香和溫柔的空姐喚醒,模仿著周圍的人開啟了前方的小桌板,要了一份飯與一杯飲料。迅速而又不失禮貌地喫完之後繼續閉眼休息。
飛機降落前強忍著睡意睜開了雙眼,這才注意到窗外已經能夠清晰地看見大海了。很藍很廣闊,海天一線的景色,讓出生在內陸的我著實有些激動。
「你是留學生?在東京嗎?」鄰座傳來的聲音。
睡了一路,第一次正視身邊坐著的人。「我是第一次來,來東京讀日語學校。」我解釋道。
「看你睡了一路,完全沒有第一次出國的那種緊張感,所以還以為你是回國探親返校的學生呢」。旁邊的先生說完大笑了起來。
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也有點小竊喜,看來我表現得足夠鎮定。心裏面給了自己一個個小小的褒獎。
之後,鄰座先生很熱心地給我普及了一點「生活小竅門」。比如手機可以去辦理au公司的,因為這家公司有針對學生的優惠套餐;辦理銀行卡儘量要去三大銀行辦理……等等。
不久,飛機成功地降落在了成田機場,著陸時身體隨著機身沉了一下,隨著那一沉,一直懸著的心也變得踏實了。因為校方說,會派人來接機。
謝別了鄰座先生,跨出了機艙門。心裏默唸:你好!日本。
未完待續……
供稿:安寧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