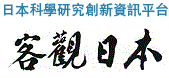我去春帆樓那一天,恰是個歲寒的日暮。春帆樓負山面海,前有江海滾滾,後有山林藹藹,曉月就落在那樓前的松樹上,令人不禁想起「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的詩句。
李鴻章李大人當年簽署「馬關條約」的小旅館已於1945年毀於大火,今日可見的是在原址上修建起的兩層木頭結構小樓,其門右側豎著一塊長條木牌,寫著「日清講和紀念館」。

紀念館一樓正中,是被四面落地玻璃永遠定格的歷史空間,也就是李鴻章父子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談判的現場。寬大的長形談判桌上罩著天藍色綢緞,一把有扶手的紅靠椅是李鴻章的專座。專座右手邊還放置著一個繪有圖案的瓷痰盂,而其他人則沒有這個「優待」。

有一說是吳汝綸在李鴻章逝世後東遊日本,也專門到春帆樓走過一趟。他見李大人的椅子比其他人的矮半截,不禁悲從中來,寫下「傷心之地」這四個字。而我今日所見,竟非如此。李大人的椅子之所以矮,是因為日方專門為其準備了有扶手的軟座,彰顯其地位高於他人。再想那李大人身高六尺有餘,即便坐下也不見得會比他人「矮半截」。


但聞「感時花濺淚」,觸景生情,移情於物,如此談判場景看在眼裏,此時此地,能不同此傷心?這「馬關條約」可謂是中日兩國近現代發展的分水嶺,上邦老大國自此步步沉淪,東夷小國從此走向富強。
儘管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同被譽為「東方俾斯麥」,儘管伊藤博文承認,如果換自己在中國,絕對做不到李大人這般好;如果換李大人在日本,絕對做得比他伊藤博文好。但這二人直接對弈的結果,卻被永久刻在春帆樓外的「講和碑」上。李之恥辱,即是伊藤之榮光。
《馬關條約》裏規定的清朝賠款,超過日本3年財政收入總和。日本扶桑社編輯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中也明確寫道,日本「重工業的投資來自於下關條約(即《馬關條約》)的賠償金)」,承認日本是靠清朝賠款開始了產業革命。「講和碑」對此也毫不諱言,上刻「嗚乎,今日國威之隆,實濫觴於甲午之役。此地亦儼為一史蹟,其保存豈可附忽諸乎?」
「講和碑」不諱言的不僅是賠款興國,也有這春帆樓的前生今世,逸事浮名。春帆樓最初是一寡婦所開的小旅館,吸引到不少商人鄉紳前來投宿。「寡婦某營客館,縉紳多投於此」。如今的春帆樓也是個華麗大方的客館,雖不是寡婦經營,卻依舊有縉紳投宿於此,就連歷屆日本首相途經下關,都不忘在這裏聚餐或住宿,比如竹下登和安倍晉三。

在「日清講和館」的對面,還有一條曲徑通幽的小路,指示牌上寫著「李鴻章道」。這是李鴻章被日本浪人小山元之助開槍射中面門後,日方專門為其開闢的。小山雲之助的開槍走火,逼得在談判中處於上風的日本不得不對清朝無條件停火,無怪乎至今都有網民在喊「憤青誤國」。而李鴻章留下了那件染滿老臣碧血的朝服,相信「此血所以報國」,卻隻換來西太后輕描淡寫的一句「難為你還留著」。
二十歲的李鴻章曾在北上求仕前豪氣萬丈地寫下「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但經春帆樓談判一事後,李改吟「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略有李斯黃犬的味道。《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在乘船回國之際,曾眼望春帆樓起誓,「此生永不再踏日本國土」。奈何,「海外塵氛猶未息」,他出使俄國,必須取道日本。老大人換船之際不肯上岸重履日土,遂令手下人在兩船之間搭一木板,弓背縮腿,顫巍巍戰兢兢地爬了過去。
一人豈能賣一國,然而總要有人為大清背鍋。這翻手雲覆手雨的人世間啊,對李鴻章的評點從未中斷。毀則說其醉心功名愛惜毛羽,譽則贊其千百年獨此一人,公道點的說是弱國無外交。吾輩敬其才,惜其識,悲其遇,因此在這寒風裏,明月下,春帆樓前,再嘆一回裱糊匠。
供稿 莊舟
編輯修改 JST 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