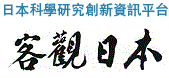狐狸烏冬麪與宮澤賢治筆下的狐狸幻燈會
韓國的朋友告訴我,剛到日本時最大的「震驚」是滿街的「狐狸烏冬麪」、「狐狸蕎麥面」等狐狸系類,在韓國作為「狡猾」的代言人的「狐狸」,為什麼在日本會與美味料理聯姻呢?朋友為「狐狸」這種動物在日韓兩國各具不同的定義和身份而驚嘆。

日本家喻戶曉的「狐狸烏冬麪」(示意圖)
其實,我也產生過同樣的疑惑。那還是在國門尚未對外自由開放的一九七九年,我在位於重慶的四川外語大學念研究生的時候。那個時代,還沒有健全輸送外國出版物和資訊的渠道。我有幸得到了宮澤賢治胞弟宮澤清六從日本寄來的宮澤賢治的作品集,並為作品中的 「狐狸」形象所震撼。
震源發自宮澤賢治(1896—1933年)的名作《過雪地》。「大雪牢牢地凍了起來,比大理石還硬,冰冷的夜空就像光滑的青石板鑄成」,在這樣的一個日子裏,「四郎和寒子穿著小巧的雪履」,咯吱咯吱地在原野上行走。被兩人的腳步聲所吸引,出現了一隻名叫紺三郎的白色小狐狸。於是,在白雪皚皚的森林中,四郎和寒子應邀參加了由狐狸舉辦的「跨文化交流」幻燈會,和狐狸們對歌共舞,不知不覺中相互建立了純樸而誠摯的友情。狐狸們還端出黍膏團來招待他們,卻又擔心他們是否敢喫。當看到兄妹二人把黍膏團一掃而光後,小狐狸們高興得又唱又跳——「從此我們不再騙人了」。兄妹二人感動得淚流滿面,還收下了一堆板栗作為伴手禮帶回家。這場「異想天開」的雙向感應共鳴的聯歡會結束之後,小兄妹被狐狸們依依不捨地送到了林外。

宮澤賢治的胞弟宮澤清六贈送給筆者的宮澤賢治作品集
《過雪地》通過孩子和「狐狸」之間的深水層融合而闡述了和合的思想、和合的哲理。然而,這一表現手法令我感到意外。因為,這種人物設定和描繪運作遠遠超出那個時代的一般中國人的習慣想像。中國的狐狸大都是不受歡迎的反面形象,數千年來一直扮演著動物中的次品。而日本人對「狐狸」的信任度和親近感也與中國人大相徑庭。因此,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電影《狐狸的故事》(キタキツネ物語)在中國上映時也曾引起轟動——其擬人化的敘事手法讓當時許多人感嘆:原來狐狸不止是狡猾的代表,也懂善意,且有可愛的一面。
相對而言,「狐狸」在中國民間並不具備光輝的形象,在韓國也同樣被認為狐狸是奸猾的象徵。在韓國,狐狸也是招人嫌惡的動物。善於賣弄風情的女人在韓語中被叫為「yo-wu」,即狐狸精的意思。在韓語裏,「鏈段運動尾巴」這一說法等同於中文的「飛媚眼」。韓語中的「kumiho」就是指化身為絕色正妹的狐狸精,據說她能勾引男人並吸光其精氣,從而使自己壽命可達千年之久。
人們之所以容易聯想到狐狸的的劣跡,與驗證狐狸劣根性的文獻不無關聯,而這類文獻大都源於中國的古典。日韓兩國自古以來都濃重的吸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攝取吞吐過程中也自然接收了「狐狸觀」的出沒潛入。
因而,當看到宮澤賢治所描繪的孩子與狐狸之間相處水沫相如的場景時,不得不感嘆中國與日本對「狐狸」的「料理」效果實在是有著天壤之別。中國與日本雖同為漢字文化圈的近鄰,日本自覺主動地選擇了接受中國文化的燻陶器而走向文明的道路,然而僅僅透過「狐狸」觀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中日之間的確存在著似同而異的文化差別。
1981年秋天,我所提交的畢業論文内容是「試論宮澤賢治筆下的動物」。在宮澤的筆下,動物們就像是生活在另一文化圈的生物,它們和人類一樣具有同等的智慧和共性,顯然,基於這樣的定位而展現作品的精神世界是宮澤賢治文學的特點之一。這篇以動物形象為研究資料的論文,沒想到竟然成為了新中國第一篇研究宮澤賢治的學術專論。在此基礎之上,我不斷將宮澤賢治的作品翻譯介紹到中國,並在2000年以《宮澤賢治與中國》的研究為題,被御茶水女子大學授予了人文科學博士學位。

筆者翻譯出版的宮澤賢治的部分著作
我認為宮澤賢治借用動物想要傳遞的是,尋求不同文化區域間的和諧互鑑,必須具備知己知彼的願望和姿態。生物與生物、生物與自然,世間萬物都肩負儘量減少誤讀,相互認識和理解的宿命,只有「識天命」,才能維護無限循環的命運鏈結,那是無法擺脫的共生式命運空間。就這樣,宮澤賢治作品中的「狐狸」讓我體味到「宮澤賢治的衝擊」,極大地刺激了我參與日本社會,研究日本同時也研究中國的好奇心。
日本狐狸觀的文化背景
童話作家新美南吉(1913—1943)曾經寫過一篇《買手套》的童話。眼看著嚴冬就要來臨了,狐狸媽媽要給孩子買手套,於是便來到了人們居住的集鎮。她對孩子說,人類很可怕,並把孩子的一隻手變成了人手,告誡孩子說,只能伸出這隻手去買手套。可孩子卻沒有做到,結果被店主人給發現了。幸好店主人很同情這隻小狐狸,裝做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照樣把手套賣給了小狐狸。這和對九尾狐精心存善意的做法可謂是一脈相承,從中可以感受到日本人對動物的溫情。
諸如此類,在很多日本的傳說故事中能為彼此敵意的雙方提供了一個以情相見的平台。從中也可以看到,在日本,動物和人類是被同等對待的。將動物和人都作為「生物」而一視同仁的觀念自古就滲透到生活習俗層面了。
在日本,人們還把狐狸視作神的使者——斡旋豐收的稻荷神來供奉。日本全國隨處都能看到門口立有紅色鳥居(立於神社門前,形似牌坊)的稻荷神社。江戶時代的民謠——「伊勢店,稻荷院裏小狗便」——就是將伊勢店、稻荷神社和小狗這三種隨處可見的東西並列傳唱的。在江戶舊城的808個町中都建有稻荷神社。直至今天,日本全國各地的稻荷神社總共有3萬多家,約佔日本全部神社總數的三分之一,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民眾家裏供奉的稻荷神和路邊類似於小祠堂一樣的稻荷神社。人們公認位於京都的伏見稻荷大神社(始建於公元711年)是所有稻荷神社的根據地。

京都伏見大社裏口銜稻穗象徵豐收的狐狸
對處於農耕文明階段的古代日本而言,稻荷神是很重要的神靈。同時,稻荷神社還是日本真言宗開山祖師弘法大師(空海法師)所建立的京都東寺的鎮守神社。隨著真言宗在日本的傳播,對稻荷神的信仰也廣泛地向各地傳播開來。到了室町時代,工商業的興起使得稻荷神由農耕守護神兼而成為產業守護神、商業守護神,進而被奉為「衣食住的大神,萬民富足安樂的大神」。稻荷神的足跡也由農村邁向了城鎮,從平民階層進入到武士上層社會。真言宗對稻荷神信仰的傳播可謂是功不可沒,而備受真言宗尊崇的荼吉尼天正是自印度騎著一隻高貴的白狐而來的。他春天下山,為的是保護農田,秋天則在豐收後才回到山中。人們很容易將其與狐狸的生活習性聯繫起來,於是對荼吉尼天的崇拜就逐漸演變為對狐狸的尊敬了。正因為如此,位於愛知縣豐川市,供奉荼吉尼天的妙嚴寺(又被稱為「豐川的稻荷神社」)受到日本全國信徒們的頂禮膜拜。
自古以來,每當天空中出現半邊晴朗半邊雨的自然現象時,人們就會認為這是狐狸所施展的魔法,並視之為吉祥的象徵,親切地稱之為「狐狸娶親」。還要舉行祭祀活動,這種風俗一直延續到了今天。比如在山口縣下松市的福德稻荷神社,每年都會為感謝稻荷神帶來五穀豐登而舉行「狐狸娶親祭祀節」。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在群馬縣高崎市箕鄉町和新瀉縣阿賀町,每年也都會舉行「狐狸娶親」的祭祀活動。
在科學昌明的今天,日本的年輕人竟也還會時常談論起「狐狸火」(鬼火、幽靈火)。在深山或沼澤,每逢雨後的夜晚,在黑暗中就會飄蕩著青白色的磷火光,據說這多少也和「狐狸娶親」的現象有些關聯。在岐阜縣飛彈市古川町至今都還每年舉行「鬼火節」。
日本人不但愉快地接受了有關狐狸的種種傳說,還將其演變成各種節日,為生活增添樂趣。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日本人已經把人和動物之間的互動交流習俗化了,並在這樣一種沒有任何牴觸情緒的文化氛圍中豐富著自己的生活。
中國的「狐狸家譜」
讓我們順便簡單瞭解一下源自中國古典的狐狸定位。
據古代文獻記載可知,中國也並非從來都把狐狸當成不詳之物。《禮記》中就有記載「狐乃仁也」,意思是說狐狸本是有德之物,堪為人類之楷模。《禮記》一書收錄了從周朝至秦漢時期的古代禮儀,並據此加以闡釋。在成書於秦漢時期的古代地理文獻《山海經》裏也把九尾狐狸精當成「靈物」加以記載。由曾任秦國宰相的呂不韋主持編纂的《呂氏春秋》中也把狐狸稱為「瑞獸」,其記述如下:「塗山人歌曰:‘悛悛白狐,九尾煌煌,如家就室,倡我都邦’,祈願為塗山東牀」。
但這種對狐狸的好感自漢朝以後就逐漸逆轉了。在成書於東漢初期(公元100年左右)的中國最古老的字典《說文解字》當中,對狐狸的註解已經變成了「妖獸」。
整個東漢時期(25—220年)是儒家學說日漸昌盛的時代。此時距孔子開創儒家學說已歷經數百年,即便是從西漢漢武帝(前156—前87年)把儒家學說奉為「國教」之時起算來也又過了200多年,儒家的學說思想已經深入人心。而儒家的理論講究非黑即白,渭涇分明,對人對事都必須基於倫理道德而得出判斷,絕不容許不講原則。於是,對於禍國殃民的九尾狐的印象一經定論就絕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了。
東晉(317—420年)時的志怪故事集《搜神記》(於寶著)中這樣寫道:「狐狸乃先古之淫婦也」。而作為中國正史的二十四史中的《晉書》中亦寫到「狐幻化以惑人」。晉朝(265—420年)是繼三國之後,取代魏而建立的統一王朝,但關於它的正史則完成於唐朝初期。由此可以看出,在唐朝時狐狸已然完全被視作邪惡的化身。有關狐狸的傳說在唐朝時特別地流行,現在看來都是一個模式,即狐狸精化為正妹而坑害男士。
宋朝(960—1279年)的《太平廣記》中有關狐狸的傳說完全承襲了唐朝的模式。《太平廣記》成書於公元978年,是奉旨欽定的鴻篇巨著。全書共500卷,從475種古書中拔粹編輯了包括奇談、異聞在内的各種傳說,在内容上與日本的《雨月物語》(成書於1776年,上田秋成著)類似。而明朝的《封神演義》則沿襲《太平廣記》的風格。
白居易(772—846年)的詩中也有「古塚狐,戒豔色也」的詩句,告誡人們不要貪圖美色(古塚狐,千年老妖為美婦,容貌姣好,頭作雲鬢面為妝,大尾曳地化紅裳……)。詩歌反映的是化身正妹的狐狸精,能讓男人們心馳神往,樂不思家,就如褒姒或妲己一般「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所以,「狐狸精」也就成為了「傾國傾城」的魔女的代名詞。
清朝的蒲松齡(1640—1715年)更是為狐狸精的形象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蒲松齡窮其一生寫就了以神仙鬼怪、妖精狐仙為主要題材的《聊齋志異》。這部不朽名著多達120萬字,共由431篇短篇構成,其中圍繞狐狸精展開的故事實在是不少。但是在蒲松齡的筆下,狐狸們對當時的社會道德觀進行了強烈評擊和諷刺,從而也對長久以來的狐狸精的負面印象起到了修正的作用。
類似這樣的民間傳說在韓國數不勝數。由此不難看出,韓國亦深受中國文化中九尾狐傳說的影響。實際上,韓國作為儒家文化圈的國家,自古以來就被稱為「儒教模範之國」,所以對於九尾狐的印象與中國類似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許可以理解為是儒家學說價值體系作用之下的「意外」結果吧。
「狐狸」的形象和特點在中日兩國文化中的不同變遷,顯示了日本與中國之間文化上的交錯與融合形態的多姿多味。是「狐狸」開啟了我考察文化交流、文化混合、文化交叉的契機。中日文化的同文可以共同歸結到「漢字文化圈」,而中日文化中存在著的相互差異則源於互為中心的區域文化之交錯。中日間的文化關係像分子與分母,有和也有分。對日本文化瞭解的越多,越會發現理解的不夠深刻,大概 「知」之本身就是對「未知」的一個認識過程,而這個過程正是無止境的文化之旅。具有對日本的調查研究以及生活體驗的積累的人都將有所自覺:讀解日本的同時,也是讀解中國的「雙向」過程,是一種自發的「對應的相互探討」。
因此,援用比較文化的手法對兩國的歷史社會文化生活予以到位的調研與梳理,發揮兩國人文交流成果之正能量,以激活相互學習的智慧,升騰為相互發展的動力。其成果不僅可以促進兩國國民的相互理解,同時也有助於雙方各自的自我反思,溫故創新。
文/圖片:王敏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