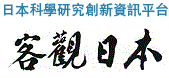鼠去牛來,舊桃換新符。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並沒有同2020一起成為過去,反在年初當頭棒喝,再次啟動了「緊急事態宣言」。疲乏的日本民眾,在一年來的慢性防疫的過程中,已經失去了首次「緊急事態月」裏的那種警惕性。
不知道《客觀日本》的讀者們是否還記得河野先生,那位池袋亂步道上的烏冬麪店主。去年4月,他在店門口豎起一塊小白板,上面寫著,「好消息,房東出於好心,疫情期間降低了房租,我也想將這份好心與大家分享,每週一全品一律便宜50日元,到6月末為止。」 這份善意的循環,成為疫情寒潮下的一股暖流(參見:【新型肺炎】疫情下的小店主,一個人活成一股暖流匯成一片大海 )。

河野先生來自有「烏冬之鄉」美譽的香川縣,從1990年就在亂步路上開店,小小的門面,豎著一塊純木的看板「四國名產 贊岐烏冬 河野」。烏冬麪是每天早起手擀的,烏冬湯是用片口鰯的小魚乾現熬的,一鍋湯大概是100碗的量,所以每天就售出100碗麪,售完關店,到了第二天繼續重複這一循環,兢兢業業30年。
不過河野先生也不是沒有故事的老同志。他年輕時上京打拼,逐漸撐開場面,在經濟高度成長期的餘暉裏,於歌舞伎町經營一傢俱樂部10年,據說做得不錯,就是約束年輕姑娘們太難。
風起雲湧千帆過盡,河野先生組建起了自己的小家庭,於是徹底告別浮華的生活,在池袋的亂步道上開出了烏冬麪店。至於為什麼是烏冬麪,他說:「上京以來喫到的烏冬麪,在我們香川縣出身的人看來,統統都是冒牌貨(笑)。」

烏冬麪店距離立教大學很近,最便宜的素烏冬400日元一碗,吸引了很多求學的苦寒學生。對於持學生證的大學生,河野先生一律打折。
在店門口,有一把小小的摺疊椅和一張木面的小圓桌,上面放著一個碗大的玻璃菸灰缸,是他自己小憩用的席位,在店門内,三條長木桌,最裏面一個一字型廚房,很像昭和時期的食堂。

早上經過時,通過開著的玻璃門,可以看見河野先生在廚房裏擀麪熬湯的身影,下午經過時,偶爾會看見河野先生坐在門口抽上一支小憩,享受難得的空閒,彼此點個頭問候一聲,到了晚上9點多,隻剩廚房裏還亮著燈,又瞥見他一個人忙碌的背影。如此一個清剛、寡言的老派硬漢。
許是因為客源的減少,去年9月的一天,店面拉下了鐵簾,貼出了字條,「因為個人原因,休店一段時間,11月再開。」
我也就安安心心地等著。2個月很快過去,11月來了,河野先生卻沒有如約開店,不免就有了擔心。我家先生安慰我,「大概是見沒生意做,索性暫時搬回了鄉下,以侍弄田園為樂,辛勞這麼多年,正好趁機清閒清閒。」

會嗎?我問自己。河野先生不像是食言的人,也不會不打個招呼就無故失約。但同時我又知道,搬到鄉下遛狗種菜,松花釀酒,春水煎茶,是我家先生的夢想。他把自己心中對晚景最好的想像,都投射到了河野先生身上。我們都是發自內心地希望,河野先生能在遠方的香川縣,過著那樣的小日子。
12月的一天清晨,在行進的巴士中,我看到烏冬麪店的鐵簾捲起,裏面還有燈光,大喜過望。河野先生終於回來了,就說他如何捨得下這30年的小店!到了中午,帶上先生約上朋友,興沖沖地趕過去,結果,鐵簾又恢復了原樣,早上看到的那一幕,竟像是幻覺。「大概今天是來收拾一下,準備正式再開吧。」朋友說。
遂又安安心心地等著。直到,直到那一天,看到店門大開,店内幾位裝修工人在有序地忙碌著,心中大駭,不由地就急了,「河野先生呢?這是在做什麼啊。」和善的負責人說,「聽說店主去世了。」見我眼淚出來,又趕緊解釋,「對不起啊,我也是聽他家人說的,我什麼都不知道的。」
逝者如斯,多少人永遠地留在了2020,成為昨日世界的一部分。然而若干年來猶如街區地標般存在的人的離世,實在是比遠方親友的噩耗更令人感受深切的,越發覺得人生苦短,如露亦如電。

還是那條路、那個店址,但河野先生的痕跡已經被全部抹去,就彷彿這家店、這個人從來都沒有存在過。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延展閱讀
【新型肺炎】疫情下的小店主,一個人活成一股暖流匯成一片大海
文 莊舟
編輯:JST客觀日本編輯部